找人做了三场直播,成本花了9万,最后亏了5万,做珍珠生意的刘先生感觉自己在找主播这件事上运气不太好。
要说2020年最火爆的商业形式,非“直播电商”莫属。不论是疫情的爆发催生了一个“全民直播”的新时代,还是在新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直播带货”成了新风口。一场直播,动辄几百万、几千万的观看量,甚至上亿元的成交额,这无疑是让任何一个品牌商家都要眼馋的“流量池”和“交易场”。
然而,众多看似火热的直播间,也往往让商家们虚实难辨。“自己很难判断,他们(主播)很多数据都是做出来的,过来赚个出场费。”刘先生如是说道。这种现象导致的结果就是,众多和刘先生一样的小商家原本寄希望通过直播带货实现的销售额不仅无法实现,甚至完全无法覆盖主播的出场费。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能让商家把‘坑位费’(出场费)挣回来,就算是很有良心的网红了。” 经手过上千个网红带货案例、深谙网红运营的一位MCN机构负责人对每经记者直言。
记者近日通过多方调查采访了解到,实际上,在火爆的直播带货背后,像刘先生一样“高坑位费低销售量,商家不赚反亏”的直播间案例不在少数。同时,主播带货之后,部分退货率高达50%以上,也让商家们叫苦不迭。
理想和现实巨大反差背后,屡禁不止的刷单“灰产”正在重新活跃,直播间粉丝、点赞、人气、评论皆可刷。 增粉100只要8元、“1288赞+88条真人评论+10万播放”只要30元……更有甚者,仅靠一个刷单软件,粉丝评论、互动、销量甚至发言的间隔时间,便可以随意设置。
“刷单已经是行业内的普遍现象了。” 这是多位行业内人士无奈的共识。
高“坑位费”低销售量,商家不赚反亏
来自浙江的刘先生(化名)做珍珠生意好几年,一直销量平平。去年,他看到自己做生意的朋友一个月内请了两三个主播为自己带货后,销量不错。心动的刘先生便通过朋友介绍、微信联系的方式前后找到了三个主播为自己带货。
然而,出乎刘先生意料的是,这几次直播体验不仅没为自己带来净收入,反而让自己亏了不少钱。
“我觉得找主播是要看运气的,我运气可能就不太好,三场直播下来,我的总账是亏的。”刘先生说,“我通过朋友找到了一名主播,出场费8000元,但最后只给我卖出3000多元的货, 当天晚上对方来我场地直播了5个小时,就是这个效果。”
据刘先生介绍,这位主播与刘先生协商的是“出场费加20%的佣金”的形式,平时这位主播的出场费要2万,但由于该主播即将换MCN机构(团队化孵化网红,将流量变现),再加上朋友介绍,他才以较低的价格拿下出场费。
“有厉害的主播,但不是每个主播都很厉害,用我的话讲就是看运气。你自己很难判断他们的数据,他们很多数据都是做出来的,过来赚个出场费。”
刘先生自己总结了三个找主播的经验,“一种是在阿里V达人上找,一种是朋友介绍或者去微信群里找,还有一种是看直播时觉得主播效果好,自己找主播私聊。”
“但是如果做过直播,就会知道,所有的数据都可以做假的,真实的后台你不知道,所以你只能自己去判断主播行不行。”刘先生提醒道。
刘先生找的这3场直播,“坑位费”加上佣金总共花出去近9万元,但销售额并不理想,刨去各种成本,刘先生反而亏了近5万元。
图片来源:摄图网
有了此前的高出场费低销售额的经验,刘先生后来开始尝试寻找免坑位费,纯佣金的主播。“纯佣金的结果就是发了很多样品出去,有好多要么直接把我拉黑了,要么就是没有回复。” 刘先生无奈地说,“我能做的只有投诉。”
无独有偶,另一位来自上海的小宁(化名)也有着同样的遭遇。为了推广自己当时所在公司的行李箱,她以2万元的坑位费邀请了一位旅游博主以期实现销量。
“我从十几个旅游博主中选中的他,他之前的直播数据、社交平台的数据很漂亮,但最后一件商品都没有卖出去,我们平常自己播还能卖十几件。”小宁对记者如是说,“博主估计也挺不好意思的,后来还附赠了我们微博、马蜂窝等好几个平台的品宣稿,我们就当作品牌曝光了。”
尽管博主事后仍有补救行动,但这场零销售额的直播还是让小宁记忆犹新。
部分主播退货率高达50%以上
不仅如此,记者进一步深入调查了解到,刷单带来退货率居高不下的例子也屡见不鲜。“主播刷单一时爽,商家退货泪两行”,刷完单的主播拿上坑位费就跑,只剩商家来收拾退货“烂摊子”。
甚至有商家表示,自己找的纯佣金主播,虽然未收取坑位费,但“当天成交订单,第二天退了90%的货”。
资深电商运营人员小鱼也透露,“有一些主播,坑位费找你要5万,然后拿3万去刷单。”
“我听别人讲有些主播退货率就很高。而且有些卖家是中间商,没有自己的实体店,结果一退货全压在自己手上。”刘先生说。
有行业人士向记者透露,一般退货率50%以下的佣金不作退还。 另一位从事电商运营的人员则告诉记者:“有些要坑位费的中小主播的退货率高达50%以上,这种好多都是刷单的。”
除了刷单带来的退货,还有部分退货与商品宣传、商品类型有关。
中国消费者协会3月21日公布的《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从目前直播电商销售商品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性质来看,有两点被提到的次数比较多:1.主播夸大和虚假宣传、2.有不能说明商品特性的链接在直播间售卖。
一位从事电商运营的人员表示,“不要坑位费的主播,基本退货率需要看商品类型,大部分退货率在5%-15%。”
针对直播带货的退货率,某电商直播业务负责人段先生(化名)认为,带货直播的给予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时间很短,这里面包含了消费者的冲动消费在内,事后觉得并不需要而形成的退货。此外,当收到货品后发现实物与期望之间不同的时候,会产生一种落差,而货品本身并不存在问题,这也会造成退货。
《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显示,有37.3%的受访消费者在直播购物中遇到过产品质量问题,仅有13.6%的消费者遇到问题后进行维权投诉,维权率过低更会滋长假货漫延。
图片来源:《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
“当然,不排除一个快速发展的行业或多或少存在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现象。比如主播对产品特性了解得不够透彻,在推介过程中造成偏差,从而形成售后问题。甚至可能部分存在夸大和虚假宣传。”段先生表示。
图片来源:《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
记者根据与商家的交流,总结了他们对直播带货最常见的几类吐槽,你有遇到过吗?
人机粉丝混合真假难辨、刷单套餐五花八门
“郎有情,妾有意”,商家与主播之间多数是一种互选关系。但在如今,随着MCN机构数量的暴增、网红经济逐渐发展,商家对“带货主播”的能力要求愈高的情况下,主播间的竞争也显得愈发激烈。
漂亮的数据和良好互动甚至成为部分主播与商家谈判的谈资。而这除了与主播自身的业务能力有关之外,还不得不提到“刷单”。
在每经记者近日多方深入调查中发现,如今直播刷单的方式、套餐已是五花八门。
“粉丝我们这目前有两种,高端粉丝25元100个,纯真人粉丝60元100个。”一名刷单贩子向记者介绍,高端粉丝是人机混合粉丝,真人粉丝与机器粉丝的混合比例为五五开。 当记者提出,此类粉丝是否会被查出时,其表示:“不会的,我们是被官方承认的数据。”
另一位刷单贩子售卖的则是软件,他给记者发来一条链接,有刷单需求的商家点进链接下载软件,并登录自己店铺,就可以进行操作。
“软件有直播互动的功能,很多直播间在用。”据这位贩子介绍,在他这里也可以进行刷单。“每单12元起,在软件上,您可以自己放单。”
当记者提出是否会被查时,该名刷单贩子表示,“这个不查的,你可以慢慢地递增上去,500-800-1200-2000这样子。”此外,他还表示,直播间的观看量、点赞量也都可以进行操作。
记者注意到,除此之外,观众看到的直播间里的热烈发言也有可能是机器生成的。
根据贩子提供的软件操作视频,商家在登录软件后,通过扫码,便可操纵一个账号在直播间里人工输入发言。此外,在软件里也可以设置几百句发言,以及每句发言之间的间隔时间,之后直播间便会自动跳出一条条评论,直播间的氛围看起来相当热闹。
688元每月的刷单软件截图,评论、点赞、关注、买单一应俱全。
如此这番操作之后,人机粉丝混合的直播间,让人很难分辨真假。
值得一提的是,在该款软件里,还有“去购买”一栏,商家还可以设置买单量及每单出现的时间。刷单贩子告诉记者,这款刷单软件价格为688元/月。
在另一位刷单贩子这里,“真人粉丝”则显得格外珍贵。“晚上7点到9点的真人需要提前预约,临时不排。”在这位刷单人员这里,25元可以买到抖音直播的100人观看量,但并非真人,他向记者强调,“真人观看的价格为每小时10元/人”。
记者在该名刷单人员朋友圈看到,除了抖音,他还长期承接淘宝、京东、天猫、一直播、花椒等各大直播间人气在线互动。
“我在为即将到来的618年中大促发愁。今年直播比往年都要多,618期间本人晚上6点到9点30不回答任何咨询问题,只排单接单。”他在朋友圈写道。
而在记者此后与多个类似刷单机构的咨询中,亦不乏“1288赞+88条真人评论+10万播放=30元”等更多低价位、五花八门的热门套餐。
某刷单公司发给记者的报价表
以记者找到的一家给短视频直播平台刷单的新媒体公司为例。该公司工作人员声称,自家的刷单业务为“全网最低价”,截至目前,已经有数万人在该公司购买了相应的刷单服务。
新媒体公司工作人员提供给记者的刷单业务价目表
该工作人员提供给记者的刷单业务价目表显示,其业务分为“热门套餐”与“单项服务”两大类。
其中,“热门套餐”中有例如“38圆=8888播放+188赞+50分享+10高级评论”“388圆=88888播放+1588赞+500分享+60高级评论”等服务,价格也从最低的38元到988元不等;而“单项服务”则包括真人粉丝、点赞、高级评论、播放、分享。
无独有偶,另一个专门提供快手、抖音平台刷单服务的机构客服人员任芊(化名)告诉每经记者,8元即可购买100个快手粉丝,一千以上优惠,掉粉给补。而抖音粉丝的价格更高一些,每增加100个抖音粉丝需要15元。
“抖音的相对要贵,抖音平台限制较高,难度相对来说比较高,所以收费也是不同的。每个单子,都是由一个团队来完成的,抖音资源较少,速度较慢,快手恰恰相反,就很快。”任芊说。
刷单机构客服人员表示,“掉粉”一年内包售后
“全部都是高活跃度的人工团队接单!1人1号1机1IP,百分之百纯真人。”任芊告诉记者,“要是真的注重质量,可以去平台推广,不过花销会很大。一般新号,都是有个一两万粉丝,然后再去用官方推广,效果会好一点。等到破一万粉丝,弄个蓝v认证,账号权重就会好很多。”
谁在刷单?谁的狂欢?
类似于上述给短视频直播平台和电商直播平台刷单冲量的“专业”机构,网上一搜随处可见。但是对于这些机构来说,究竟哪些人会真的自掏腰包买粉丝、刷点赞?答案似乎没有这么简单。
一位直播行业人员就向每经记者坦言,自己曾刷过单。他表示,“刷单要看平台的浮动单价,一般是按分钟付费或者定时2小时完成刷单,如果商家对你有KPI要求,那你最好一直挂着。”
一位深谙网红直播带货运营的业内人士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则表示,从他了解到行业情况来看,会选择刷单的网红主要有两类人群。
第一类人群是为了接广告 ,因为只有粉丝量高了,直播间的人数看着比较多,谈广告时才能卖得上价格。一单广告赚一两万甚至更多,就是要维持这种热度。
第二类人群就是为了卖货 ,如果说一场直播本来只能卖出100单,但是通过刷单能卖到1000单,那无论是为了接广告,或是为了收“坑位费”都有好处。
该人士的观点得到了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MCN机构从业者的认同。
“就像之前开淘宝店、开天猫店的(商家),为什么平台一直严打,但总有人刷单?其实大家都是为了达到一种从众效应。”该从业者表示,如果只是几百单的销量,那么下单的消费者往往会有疑虑,怀疑你的产品质量问题,或者怀疑你作为主播带货的信服力,但如果看着直播间里的销量快速上涨,涨到了几千单、甚至几万单,那肯定会有很多人跟风购买。
实际上,对于很多刚起步的带货主播,甚至中腰部主播来说,即便是日复一日坚持直播,想要提高粉丝数量,持续地获取到更多关注度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年1月时,一位服饰类商品带货主播的快手号关注粉丝量有24万,到如今,涨了10万达到34.1万。半年时间10万的粉丝量增长,相较于一些头部网红IP来说,可能不值一提,但这背后却是她每天早上凌晨4:00点起床开始筹备直播,深夜11点才能下班回家换来的成果。
就此而言,在线上流量成本持续走高、且直播电商市场竞争越发激烈的当下,一面是直播带货对粉丝、人气积累的迫切需求,另一面又是增粉难、人气不足的尴尬,这种矛盾便形成了大量的流量需求,而刷单就成了部分主播提高知名度的一条“捷径”。
值得注意的是,其实不只是带货主播有刷单的诉求,对于部分品牌商家来说,同样有刷单的需要。
对此,关注直播的创新工场高级投资经理王安得在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所有电商长期以来一直都有刷单的问题。而电商直播的刷单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头部网红直播刷单,第二种是商家故意通过外部工具或者机构进行刷单。
王安得进一步表示,对于网红直播刷单,这种刷单的目的在于,一场直播下来会直接拉高直播带货的GMV,但其实很多不是真实成交的GMV,当然也会包含很多用户冲动型消费。
而对于商家故意通过外部工具或者机构进行刷单,王安得称,之所以出现商家故意刷单情况,是因为现在多家电商平台站内的直播电商为了抢占站内权重,只有单量高,平台给到的流量才高。虽然很多平台内部是有一套算法体系去监控,但是刷单现象还是存在的。
此外,王安得还表示,其实还有很多电商直播的刷单行为是用来“哄投资人”的,因为业绩好,就会得到很多投资人的关注甚至投资,不过在选择直播电商项目时,投资人通常通过ITDD(互联网信息数据尽职调查)来对公司的直播数据及转换率进行调查验证。
一位MCN机构创始人的“旁白”
在记者调查采访中不难发现,不乏有将网红刷单背后的矛头直指市场MCN机构,认为一些MCN机构刷单的目的就是依靠网红的“坑位费”赚快钱。
同时,某大型MCN机构负责人也对记者坦言,品牌商在跟MCN合作时,往往会跟机构签订“保底销量”这样的增值服务。
那么,真实的MCN机构究竟如何看待刷单?
经手过上千个网红带货案例、深谙网红运营的美红网创始人王韩近日接受每经记者采访,给出了他眼中的直播刷单、以及给中小商家有关刷单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1、市场其实不如以前疯狂,凡是珍重网红IP的很少刷单
王韩告诉记者,正常按照平台来讲,直接去加一些假粉丝,这种情况其实比较少。如果平台对一个IP比较珍重、珍惜的话,都很少做这件事情(刷单),因为这会有一个严厉的惩罚措施。
而现在无论是再怎么精明的手段,哪怕是找真人去点关注,直播平台也都可以监测出来的,毕竟技术已经很发达,监测出来基本没有门槛了。
“但是他(直播平台)不一定说查封你,也不一定说罚你的款,而是直接给你做限流,这个号的权重就降低了。”
因此,在王韩看来,直播平台的主要态度还是打击,必须要保证这个平台的公平性和竞争性,否则就没人玩了。
另一方面,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个人自己玩一个号,刷个一两万粉丝对平台没有太大影响,似乎也不能说完全禁止你去做这个事情。
“粉丝量不能完全代表你的影响力。你把粉丝量刷上去,视频点赞量是不是也要上去,视频点赞量刷上去,视频的转发、评论是不是也得刷上去,那你的成本代价就很高了。而且你刷出来都是假评论,一看就很明显。” 对于这种刷单效果,王韩也直言。
值得一提的是,就刷单目前的情况来讲,王韩认为跟以前的包括一直播、花椒、映客那个时代,已经没法相比了。“那个时候刷量是非常疯狂的心态,现在(直播刷单)其实没什么市场。”
“如果你想踏踏实实去运营好一个网红的话,是不会选择刷粉的。本身你自己靠内容可以吸引100万粉丝,你干嘛非得刷个50万变成150万,对你没有任何好处,甚至账号可能被封掉,那么,你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这么大的惩罚力度,所以刷量的人很少。”
“即便你刷了1000万个播放量,刷了1000万的粉丝,商家的货一件也卖不出去,这个又有什么意义?”
“当短视频和直播变成全民的一个玩法,也就没有什么套路和秘密了,刷销量的影响现在几乎微乎其微。”王韩说。
他进一步指出,一个有几百万粉丝的号,发一个视频,如果点赞就那么几百个,恰恰证明这个号没有什么人看,他搞了这么多事(刷单),没有任何意义,还不如没有粉丝。而且大家一看你的直播、视频,就知道好还是不好。
2、“商家找网红如果只是想带货,95%以上肯定是亏钱的”,主要还是广告效应
“能让商家把坑位费挣回来,这就是很有良心的网红了。” 谈及当下火热的网红带货,王韩亦如是直言。
他举例,罗永浩卖货,王老吉一块钱一瓶还包邮,他赚钱吗?(商家)给罗永浩的价格都极低,可能是出厂的成本价,有可能商家卖得越多,赔得越多。并且,罗永浩的坑位费就有几十万。
“商家找罗永浩直播带货,如果好肯定能卖出去,卖不出去也没关系。他为什么找罗永浩呢,是为了一个广告效应,商家找李佳琦、薇娅都是为了一个广告效应。这就是商家找大网红的目的。” 王韩表示。
而对于小商家找小网红的做法,王韩也给出了他的警示。
“首先他(小网红)就要收你坑位费。能卖货的小网红收三五万的坑位费,肯定要考虑自己的利益,他也知道商家的利润、成本多少,那么他肯定要赚商家这个钱。能让商家把这个三五万的坑位费挣回来,这就是很有良心的网红了。大多数是什么呢,商家根本就卖不回来,你(商家)想在这里面钻空子是没机会的。”
那商家为什么还要找网红带货?
在王韩看来,可能那也那没有别的办法了。“他(商家)听着网红出货量很大,被‘绑架’了。”
“所以,所有的商家找网红,你只要是想让他帮带货的,这种想法都不可取。如果说是想找网红给你去冲一冲销量,打个爆款,然后做点广告,这个想法是可取的。你最起码能从网红那儿获取一些种子客户。获取1000个种子用户,这些客户还可以复购,还可以放繁衍出来1万个客户,有这种想法还可以。”
“这个市场已经很成熟了,不像最开始说网红不知道自己的价值,你给他很少的钱,然后他给你卖了几百万,这种概率极低,1%的概率,这种运气成分很小的。95%以上肯定是亏钱的。”说到这里,王韩不忘强调,这是他们经过上千个网红带货的案例总结出来的,是没有偏差的。
为什么李佳琦直播带的货性价比这么高,因为他有很大的流量,可以跟商家谈一个很低的价格,可以从商家那拿广告费、拿福利。
其实这个时候买货的这种行为,就变成了一种购买广告的行为了,商家找你带货,也变成了打广告的行为。那最后又变成,小商家就没有这个门槛挤进来,只有资金雄厚的大品牌才能玩这个游戏。问题是很多小商家在这个套路里面就进去了,吃亏了。
所以,小商家必须要想清楚,花10万、100万找网红的目的是什么? 王韩说,如果你的目的是为了把品牌做起来,那你就去做;如果说纯粹为了带货去库存,你就不要做。否则,你还不如自己花钱把你自己的产品买了。
虚假繁荣无益于产业生态,监管已在路上
不可否认的是,国内直播电商的前景可观。iiMedia Research(艾媒咨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直播电商行业的总规模达到4338亿元,预计到2020年规模将翻一番。同时,艾媒咨询预计,到2020年中国在线直播用户规模将达到5.24亿人,涵盖游戏直播、秀场直播、生活类直播、电商直播等。
但在直播电商市场规模急速扩大的同时,刷单造假成为业内公认的“潜规则”,这种繁荣还有何意义?
“直播主播为了数据好看,搞个几十万或者一两百万的粉丝,但这种变现能力特别有限,就算是卖点衣服等低单价商品,也不会卖得好。”王韩告诉每经记者。在他看来,但当前时代下的网红经济已经不同于以往,已经不是走“量”的时代,对于MCN机构来说,更应该去经营一些比较大的IP,把主要精力集中去做专项的和垂直的IP,挖掘一个IP更大的价值。
回归到直播带货这件事上,王安得也告诉记者,“网红直播卖货退款率平均要达到30%-40%,不过这还仅是因为消费者冲动性购买造成的刷单情况,而恶意刷单的因为平台差异很难有具体的统计数据,但这无疑会引发整个直播电商行业的劣币驱逐良币。”
图片来源:《直播电商购物消费者满意度在线调查报告》
实际上,刷数据造假的行为不仅可能会使商家的利益受损,同样也可能消磨掉消费者对于主播乃至直播平台的信任。也正因如此,不论是直播电商平台或是短视频直播平台,都对数据造假行为进行严打。
对此,淘宝直播 方面接受每经记者采访表示,从2016年淘宝直播创立以来就非常重视避免数据泡沫。一方面,平台建立起了完善的机制,防止刷数据。同时,淘宝直播还依托淘宝平台完善的机制,组织打击刷单、数据造假等现象。另外,对于淘宝平台上部分商家存在售卖所谓“刷数据机器人”的商品,淘宝平台已经进行了多轮打击。
“对于数据造假的态度是绝对零容忍,因为只有真实的数据才能带来健康的发展。”京东直播 相关负责人也告诉每经记者,京东直播从创建初期就十分关注数据真实和数据健康,并已经从技术和规则层面进行双重约束。其中,技术层面京东直播已经接入了一套严密的防刷体系,对于数据造假进行实时拦截。另外,在规则层面,京东直播也同步制定了严厉处罚举措,对于数据造假的商家、机构、达人,依据情节轻重予以处罚,严重者将永久封号。
据了解,京东直播此前在内部还成立了“风控项目组”,专门针对直播全流程接入反刷系统,进而打击数据注水、数据造假等一系列行业乱象行为。
不只是直播电商平台,对于短视频直播平台,同样也如此。
抖音 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抖音已经注意到部分黑产行业不法分子盯上了短视频直播平台,使用刷粉刷量、注册机器人账号等作弊手段,制造虚假数据,伤害了平台用户体验。而对于此类现象,抖音现已经建立了健全的识别打击机制,对数据造假等各类作弊行为进行实时拦截。对于恶意采用作弊方式刷数据的用户、机构,抖音将根据平台规则予以处罚,情节严重者将永久封禁账号。
实际上,仅在2019年,抖音就曾展开过为期三个月的“啄木鸟2019”专项行动,打击平台上的黑产作弊行为。公开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2月31日,该专项打击行动封禁涉嫌刷量作弊的违规抖音帐号203万,向有关部门举报涉嫌刷粉刷量黑产网站113家。
值得一提的是,不止直播平台的自我监管,中国首个“直播带货”标准也即将出台。
近日,中国商业联合会下发通知,文件要求,由中国商业联合会媒体购物专业委员会牵头,起草制定行业内首部全国性社团标准《视频直播购物运营和服务基本规范》和《网络购物诚信服务体系评价指南》等两项标准。
这意味着,首部全国性直播电商标准将出台,预计将于7月份正式发布执行,“直播带货”将有规可循,有据可依,正式迎来标准化发展,进入“监管时代”, 标准化“游戏规则”将助力新生业态提质增效,“直播带货”产业将结束野蛮生长,实现精耕细作。
记者手记丨直播带货,“售卖的应是一份信任”
事实上,直播这种业态形式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崭露头角,2019年也被称为“电商直播元年”。而在2020年,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宅经济”成为市场热点,企业和商家也愿意探索和尝试创新的营销模式,带货直播得到助推。
随着各大明星、网红的加入,直播带货帮助消费者缩短了选择时间,主播提前选择好价廉物美的产品,消费者只需要决定是否购买。在购买的同时还可以互动,直观生动“所见即所得”,易于被消费者接受。
对于商家而言,带货直播对于带动销量亦是有目共睹的。即便无法收获大量的销售额,面对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直播流量,也能因为一定的品牌露出以及主播的口播宣传,从而收获不错的品牌传播声量。
此外,政策支持也是直播带货火热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各地行业支持和鼓励政策不断出台。多地领导干部、央视主持人亲自直播带货,也是对这种新兴模式的认可和支持。
那么,单凭“大流量”就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带货主播”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正如某电商直播业务负责人段先生(化名)所言,带货直播的火爆与电商仓储、配送、海外通关等零售“基建”和配套政策的持续完善息息相关。
大流量只是完成了直播带货里的一个基础配置,因为有人观看才会有人购买,观看的人越多会购买的人才会越多。但是反过来说,当流量越大时,主播们与商家们承担的责任越大。
主播们售卖的不单单是物美价廉,实际上售卖的更是一份信任,消费者对于主播和产品的信任。因此,主播们应当慎重选择合作品牌,对选品环节要严格把关。商家应当规范供应链,在商品质量上下功夫,保障售后服务。
在这份责任和信任背后,切莫被刷单裹挟。毕竟,刷单互骗互害,损伤的是整个直播产业链,一损俱损,信任更来不得半点掺假和破坏。
By 高彤


















 庭秘密APP截图(受访者供图)
庭秘密APP截图(受访者供图) TST庭秘密代理业绩计算方式(图源:新京报)
TST庭秘密代理业绩计算方式(图源:新京报) TST庭秘密群聊(受访者供图)
TST庭秘密群聊(受访者供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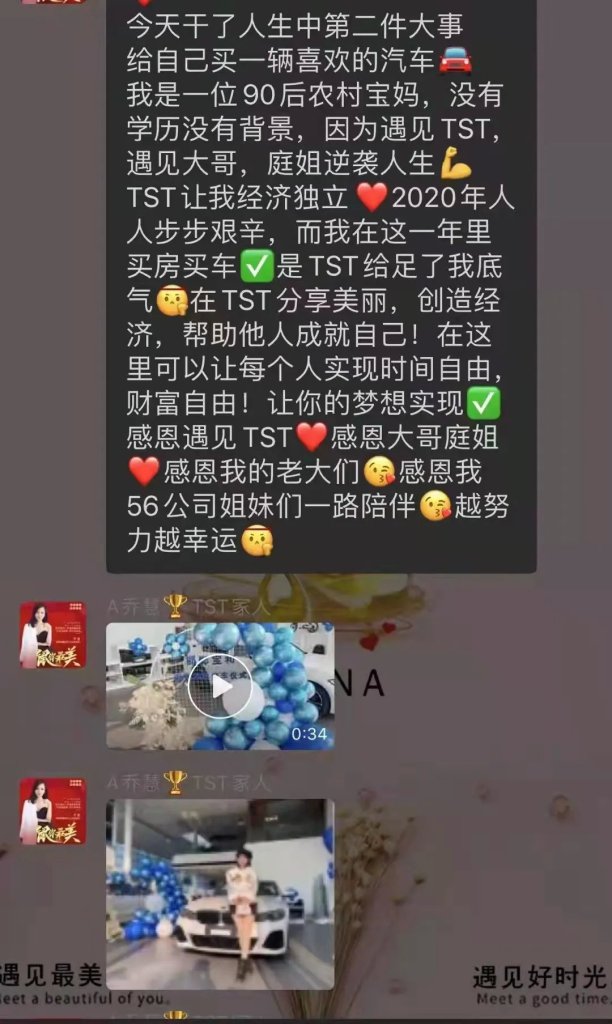
 TST庭秘密被调查(图源:中国新闻网)
TST庭秘密被调查(图源:中国新闻网)
































